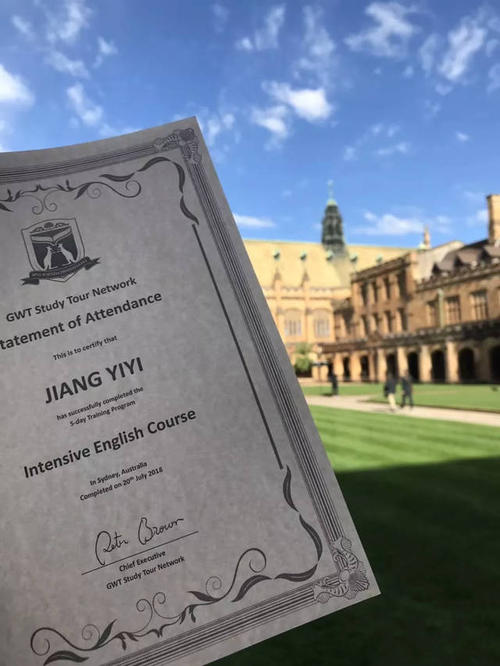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通過郭紹虞、錢仲聯、嚴迪昌等學者篳路藍縷的研究,清詩已被公認為有別于唐音、宋調,“自領一隊”。陳衍、汪辟疆、錢仲聯、嚴迪昌、朱則杰等人以詩話、點將錄、選本、清詩史著述、專題論文等多種方式,從不同層面建構清詩史,編定清代詩人的譜系序列,繪制清代詩史的宏大圖景,為新時代清詩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代詩人3萬多家,詩歌總量近千萬首。其中,清人論清詩絕句汗牛充棟,還有不少是數十上百首的大型組詩,如晚清民初詩人兼史家郭曾炘的《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續題近代詩家集后》共130首,既勾勒了清詩概貌,又凸顯了史家眼光。這無疑是清詩經典歷程的重要途徑。循此思路,我們可以重新體認清詩史,助推清詩史的重新書寫。
清詩經典化,其前提是清詩已具備了經典性。早在1929年年末,徐世昌從“詩教之盛”“詩道之尊”“詩事之詳”“詩境之新”四端闡發了清詩之“卓絕”。錢仲聯稱清詩“超明越元,抗衡唐宋”。此后,嚴迪昌又在風格的多元、流派的豐富、題材的開拓諸方面,認為清詩可以“自領一隊”。朱則杰更是謂清詩乃“中國詩歌史上第三座高峰”。蔣寅也說:“如果將清詩汰剩五萬首,其精美程度也許就不亞于唐詩。即使以絕對標準來衡量,從清詩中選五十家也不會輸于唐人的。”作為清詩一大碩果的論詩詩,無論從類型上、數量上、水平上來看,都是空前絕后的。它融通唐宋,重鑄偉辭,自成范式。誠如嚴迪昌所說,清人論清詩絕句組詩“更是不勝枚舉,不啻為一部詳盡的清詩史,對今天研究清代詩歌助益甚大”。
清人的大型論清詩絕句數量成百上千。在郭紹虞、錢仲聯、王遽常主編的《萬首論詩絕句》中,輯錄的清代論詩絕句占總數的四分之三強,數量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其中專論有清一代的,觸目皆是,如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二十首》,林昌彝《論本朝人詩一百五首》,沈景修《讀國朝詩集一百首》,彭光澧《論國朝人詩仿元遺山三十六首》,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絕句》中的《論國朝人七十四首》《補作論國朝人七十八首》,凡此種種,難以贅舉。蔣寅又在《萬首論詩絕句》之外略有補輯,如陳勱《仿元遺山體論國朝人詩二十首》等。
清人論清詩絕句的內容極為豐富。自杜甫打破“以文論詩”的傳統,開創“以詩論詩”的體制以來,論詩絕句組詩成為品鑒詩藝、摘賞佳句、月旦詩人、開立宗派、鉤稽掌故、建構詩史的一種重要體裁。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向為錢鐘書、嚴迪昌所稱引,如其一四“七子并時峙壇坫,即庵奇氣更無儕”論詩人的座次排序;其一五“楚人門巷瀟湘色,斷句流傳僅一斑”,摘名句以定詩人地位;其三四“排斥蘇詩容有說,區區鵝鴨又何爭”,論清初毛奇齡與汪琬的唐宋詩之爭;其四一“翻為虎丘增故實,虧他幕府捉刀人”,述陳鵬年詩案之來龍去脈;其四三“《秋江》神韻無人會,輕薄爭傳《香草箋》”,論爭相傳誦黃任艷體詩的怪象。舉凡詩人地位升降、詩壇重要現象、詩史關鍵事件、詩歌觀念論爭,無不入詩,靡不備具。
清人論清詩絕句的形式邁越列代。張伯偉說,“論詩詩既是文學批評,又是批評文學”,形式上有別于摘句、選本、詩話、評點。清人論清詩絕句將辭約義豐的四句,綴合成篇,連篇成章,形成首尾完整、詩旨貫通的意群世界,又在正文的基礎上加注、添序,或注出處、箋故實、釋正文、辨真偽,或記時間、敘背景、述緣由、詮義理,這些意義豐贍的副文本可與正文相互闡發。通過加注、添序,清人論清詩絕句可以有效避免吟詠對象不明、意旨不定、分析不明、體系不全的弊病。其評論形式多種多樣,仍以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為例,單就所論對象而言,不僅有只評一家的專論,還有同舉兩家的并論、囊括數人的合論、襲用史家“互見法”的分論,以及如其一詠清初南北“嶺南三家”“江左三家”“國初六家”諸詩群的總論。細言之,并論即有以祖孫、父子、兄弟及齊名詩友來論列等多種形式,如其八七詠馮浩及其二子應榴、集梧,其六九詠朱筠、朱珪兄弟,其四五詠滿族權貴鄂爾泰、阿桂,其一○一詠姨甥關系的舒位、王曇,其一○三詠詩名齊稱的陶澍、林則徐。
清人論清詩絕句是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共振,是詩心與史筆的融合。懷有濃郁“當代意識”的詩人,以史家的批判眼光,精心提煉,高度濃縮,吟詠出一部部小型清詩史,堪稱詩性敘事與史家建構的結晶。如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詠明遺民張煌言“哀猿絕島凄涼曲,蒼山還他殿有明”,可謂詩具史筆,將絕島賦詩、矢志復明的張煌言刻畫得入木三分,并認為不應列入《清史稿》,而當歸入《明史》,更展現了他的史識。清人論清詩絕句題中標識“本朝”“國朝”“近人”“近代”的,如潘德輿《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為絕句十二首》、張鴻基《論本朝各家詩二十首》、蕭重《偶檢案頭國朝名人集及近人詩箋各題一截》33首、錢樹本《讀國朝諸大家詩各系絕句》6首、王闿運《論同人詩八絕句》、沈金藻《舟中讀近代諸先生詩各題一絕》10首、張云驤《論國朝人詩》23首之類,比比皆是。清人論清詩絕句組詩大多是吟詠數十上百位詩人的佳篇巨制。以郭曾炘為例,其《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后》始自清初“江左三家”“嶺南三家”“國初六家”,下迄晚清盟主曾國藩,評論詩人170余名;其《續題近代詩家集后》專論同光時期翁同龢、寶廷、張佩綸、袁昶、黃遵憲、范當世,二者評論并涉及的詩人高達兩百多家,清代重要詩人悉數在列。
清人論清詩絕句,“采摘孔翠,芟翦繁蕪”,遴選詩人,有機序列,編成清代詩史譜系。詩史經典建構的主要途徑之一是“以人存史”,即借助詩人的經典化來建構詩史。通過比勘清人與陳衍、汪辟疆、錢仲聯等所聚焦的清代詩人,大體上可以勾勒出經典詩人名單,也可以洞察到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物。尤值得稱道的是,清人論清詩絕句精準地抓住了清詩史的兩大特征,即從地域、女性的角度別出心裁地建構詩史。前者如于祉《論國朝山左詩人絕句》12首、顏君猷《論嶺南國朝人詩絕句》15首、張崇蘭《懷國朝京口詩人絕句》12首、范溶《論蜀詩絕句》22首、廖鼎聲《拙學齋論詩絕句一百九十八首》中專論粵西的《論國朝人七十四首》《補作論國朝人七十八首》等,儼然一部部微型清代地方詩史;后者如清末福建侯官女詩人陳蕓的《小黛軒論詩詩》221首,評論清代女性詩人千余位,陳壽彭說它“有清一代女文獻十羅八九”,稱之為《清代女性詩史》也應無異議。
概言之,清人論清詩絕句價值不菲,意義非凡,將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可以提供清代詩史重建的多維視角,豐富我們對清代詩史圖景的理性認知。
(作者:謝海林,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