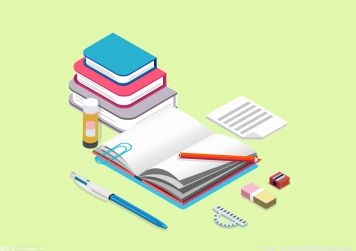(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每一次的誕生都是痛苦》收錄了詩人李少君從1980年到2022年四十余年的代表性詩作。四十年間,自然、人文、抒情成為了李少君詩歌創作中三個彼此聯結的方面,這不僅是寫作的風格,更是他的詩心、詩情、詩意的總結。
李少君被譽為自然詩人,“自然”主題貫穿他四十年的詩歌創作,他出生于湖南中部的湘鄉,湖湘風光養成了詩人的性情與文字。李少君少年時期寫作的第一首詩《蒲公英》就是他在漣水邊的一個山坡上看到四處飄落的蒲公英有感而發寫成的。李少君詩歌表現的自然是具體而飽滿的,《春夜的辯證法》中的文字仿佛一個尋找美的鏡頭,給自然中不受重視的細節一個特寫:“比如飛絮,比如青果/這些大多發生在春夜,如此零星散亂/只有細心的人才會聆聽/只有孤獨的人才會對此冥思苦想”。在《南山吟》中,詩人是云、山與遠處大海的觀察者:“坐到寂靜的深處,我抬頭看對面/看見一朵白云,從天空緩緩降落/云影投在山頭,一陣風來/又飄到了海面上”。李少君寫作自然詩并不是對現代生活的抵抗,只是寫下他在對自然的觀察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表達一種真實的體驗和感覺。
在這部詩選的后記中,李少君談及他將自然視作中國文化的最高價值,他的自然寫作不是個人化的,而是包含對世俗精神的超越,通過描寫自然表達社會性和公共性。自然的社會價值與公共意義是如何達成的?這就是他詩歌創作中人文精神的體現,他對自然的吟詠回歸到了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
正如詩人西渡對這部詩選的評語:“詩風樸拙……在當代詩歌中其技巧近乎異類。”現代詩的晦澀在李少君這里被消解了,在他的筆下,每一個日常都是詩意的,平白簡練的語言也可以有擊中人心的力量。在這四個寫作階段中,詩人關注的題材和話題在變化,在少年時期,他關注歷史人文,寫作了如《中國的月》《中國的愛情》《魏晉人》等作品,隨著閱歷增長,他的寫作開始轉向更為廣闊的世界。盡管題材千變萬化,但對人性的信任,對生活、自由和美的追求是他創作中不變的核心精神。
“詩學就是情學”,這是李少君詩歌創作的主張,也是20世紀以來,文學界和理論界一個重要的關注點。李少君在詩歌中的抒情是自發的,這既來自他對自然的愛,對人文精神的堅守,也來自他對“詩言情”這一古典傳統的堅持。這部詩選的書名《每一次的誕生都是痛苦》來自李少君青年時期的一篇作品,這首詩在傳統的愛情贊歌中獨樹一幟,他沒有寫情感的甜,而是探到了人類情感的另一面:痛苦。這讓人想起里爾克寫給青年詩人的信中所說:“愛你的寂寞,負擔它以悠揚的怨訴給你引來的痛苦。”在《寫作》一詩中,他吶喊:“寫作,你不過是我眾多惡痞中的一種而已。”在青年時代,李少君對情感的表達已有了超越性,對情感是敏銳的,亦不吝于將這種寫作中的狂熱、痛苦宣之于紙上。隨年月變遷,詩人的情感從富有浪漫氣息的狂想變成一種更為沖淡洗練的詩歌境界。《傍晚》是一首經典的抒發對父親情感的詩歌,“夜色正一點一點地滲透/黑暗如墨汁在宣紙上蔓延/我每喊一聲,夜色就被推開推遠一點點/喊聲一停,夜色又聚集圍攏了過來……父親的應答聲/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從像墨汁一樣蔓延,到明亮一下,夜色即詩情,在呼喊中時明時暗。他的情感自然、敏銳而真摯,流淌在詩行之間。
在人人焦慮于現實生活的今天,文學的價值似乎也遭受種種質疑。文學與現代生活矛盾嗎?理想是否一定與現實沖突?在李少君離開校園隨著南下的大潮闖蕩海南島時,他趕上的是海島經濟迅猛發展的時代,他見證這一經濟增速日新月異的時代,他的詩歌記錄了一個偉大時代的變遷,但同時堅持書寫自然、堅守人文理想、借詩歌傳達人類最為精微的情感。這部詩選是一個詩人對這個時代與世界的細微觀察與記錄。詩人為當下的種種迷茫指出了一條道路:回到自然中來,拾起人性的閃光,擁抱那些脆弱而無比可貴的情感,這為迷茫中的我們帶來了別樣的安慰與指引。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