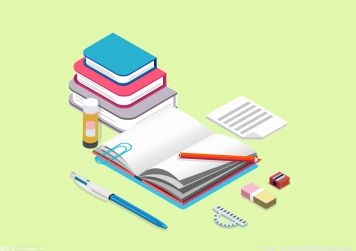5月26日,由中國輕工業(yè)聯(lián)合會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工藝美術(shù)博覽會(2023CACE)(以下簡稱“博覽會”)將在江蘇南京開幕。本屆博覽會將著力構(gòu)建工藝美術(shù)互學(xué)互鑒、共榮共進的建功立業(yè)大舞臺;構(gòu)建大師工匠興業(yè)、工美文化強國的奮勇爭先大平臺;構(gòu)建中國工藝美術(shù)聲播神州、名揚世界的高光亮麗大展臺。博覽會上,杭州朱炳仁銅藝股份有限公司將打造90平方米超大展覽空間,集中展示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朱炳仁及其子浙江省工藝美術(shù)大師朱軍岷創(chuàng)作的50件銅雕。
朱炳仁,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銅雕技藝代表性傳承人、“全國五一勞動獎?wù)隆鲍@得者、故宮博物院文創(chuàng)顧問、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文物學(xué)會文物修復(fù)委員會理事、中華老字號“朱府銅藝”第四代傳人、西泠印社社員。 ? ? ? ? ? □ 本報記者 賈淘文
 【資料圖】
【資料圖】
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朱炳仁及其子浙江省工藝美術(shù)大師朱軍岷
“在云的簇擁下,熊熊燃燒的銅坩堝,在天際線上粲粲升起,幾度登頂枕星云,須臾俯仰動金湯,通紅的銅漿滿溢出來了,潑灑著、飛濺著、噴發(fā)著,點燃了最后的夜色,熔就了生命的云彩。” ? ? ? ? —— 朱炳仁·《日出》
1944年,朱炳仁大師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市。朱炳仁的曾祖父傾一生之力創(chuàng)建了朱家銅藝,此后父傳子、子傳孫,傳到了朱炳仁大師手中,至今已延續(xù)五代。朱炳仁大師通過精心研究,將朱家銅藝雕刻留在了杭州雷峰塔、峨眉山金頂、人民大會堂香港廳銅門、G20杭州峰會會場壁畫等百余座大型國家重點的銅建筑裝飾項目之中。同時,朱炳仁大師對祖?zhèn)骷妓嚥粩噙M行整理總結(jié),使其成功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榮膺國內(nèi)貿(mào)易部首批“中華老字號”稱號,讓祖?zhèn)骷妓嚦蔀榱嗣褡宓尿湴痢?/p>
4月22日,農(nóng)歷三月初三,河南新鄭黃帝故里舉行一年一度的“拜祖大典”。當天,新建的黃帝故里園區(qū)的“兩館一中心”也在大典中亮相。朱炳仁大師及其子朱軍岷承建了尋根門、軒轅殿、黃帝文化館、中華姓氏館、游客中心等黃帝故里園區(qū)內(nèi)重要主體建筑的銅裝飾工程。他們率領(lǐng)金星銅工程的500名銅匠,經(jīng)過100余天的晝夜奮戰(zhàn),采用10萬平方米、含銅量99.9%的紫銅,以史無前例的體量與材質(zhì),將傳統(tǒng)非遺和現(xiàn)代工藝結(jié)合,用銅文化向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致敬,為中國銅工程史再添濃墨重彩的一筆。
朱炳仁大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拜祖是為了讓人們從歷史走向未來,再把自己的歷史留給后代。
在朱炳仁之前,銅作為建筑材料是難以想象的。朱炳仁大師以極高的藝術(shù)水準和科學(xué)素養(yǎng),經(jīng)歷了漫長的刻苦鉆研,最終讓銅雕作為建筑構(gòu)件體現(xiàn)出來,并實現(xiàn)模塊化、工業(yè)化,更特別的是,銅建筑的表面還有銅的肌理效果。
朱炳仁大師雖已到耄耋之年,但他卻不服老、不畏老,勇敢接受挑戰(zhàn),嘗試攀登更具挑戰(zhàn)的藝術(shù)高峰。走進朱炳仁大師的工作室,記者看到耄耋之年的“老銅匠”仍然充滿著無盡的精氣神,在創(chuàng)作中,朱炳仁大師如入無我之境,以十數(shù)斤的坩堝為筆,用近1200攝氏度的銅液為墨,在特殊調(diào)配的鋸末上凝神創(chuàng)作。一時間,奔流的銅液沖入鋸末,瞬間白煙騰起,如大霧彌散,澆筑、打磨、著色、燒制各環(huán)節(jié)一氣呵成,此時大師已大汗淋漓。
正如朱炳仁大師所說:“銅就是我,我就是銅。”?
一次偶然的機會,朱炳仁意外發(fā)現(xiàn),被烈火熔融成晶瑩的銅珠和姿態(tài)萬千的熔銅結(jié)晶體,其流暢之美是人工鑄造無法實現(xiàn)的,從而找到了創(chuàng)作靈感,他創(chuàng)立了熔銅藝術(shù),開創(chuàng)了“熔銅現(xiàn)實主義”新流派。2007年,他創(chuàng)作的第一幅熔銅壁畫作品《闕立》驚嘆世人,一面世就被國家博物館收藏。自此,他以獨特的藝術(shù)視角開創(chuàng)熔銅藝術(shù),立宗“熔銅現(xiàn)實主義”新流派。
“五千年什么文化都在變,唯獨青銅文化一直沒變,它的創(chuàng)作方式也一直沒變。但是銅在模具的圈扼中鑄造成形,仿佛成為了銅的宿命。作為一個普通工匠,我希望突破它。我不能超越和改變千年的銅文化,但是我可以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的表現(xiàn)形式,去重新演繹青銅藝術(shù)。我把銅從模具中‘解放’出來,讓銅自由流淌,讓它充分地展示上天給它的脾性。從青銅到熔銅,銅‘走’了五千年。”朱炳仁大師如是說道。
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有在生活中不斷地吸取營養(yǎng),才能讓藝術(shù)熠熠生輝、經(jīng)久不息。朱炳仁大師在熔銅藝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中采取“拿來主義”,積極吸收西方藝術(shù)的精髓,把多元化藝術(shù)精華融入到熔銅文化中,用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充盈中國傳統(tǒng)的銅文化。朱炳仁大師就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在熔銅藝術(shù)的沃土中俯首耕耘、砥礪前行。此后,《我想象中的達利》《本是同根生》《稻可道,非常稻》《入侵》《燃燒的向日葵》《地氣》《圖騰(碑)》《青花》《山水銅印》《跳舞的人》《人民的椅子》《宋畫迷宮》《春和清妍》《萬泉歸海》《清香自遠》《旌旗如山氣如云》等一大批精典力作橫空出世。朱炳仁大師帶著自己創(chuàng)作的熔銅作品走出國門,接受世界的檢閱,作品參加了多個國家舉辦的藝術(shù)展,獲得無數(shù)贊譽,被許多國家的文博機構(gòu)競相收藏。
多年來,朱炳仁大師在傳承發(fā)揚工匠精神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一步一個腳印,在技藝的創(chuàng)新中不斷謀求新突破、新發(fā)展、新作為,讓我國傳承千年的銅文化史在熔銅藝術(shù)的促進下,迎來了新的復(fù)興。
采訪的最后,朱炳仁大師感慨地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如今,‘朱府銅藝’、熔銅藝術(shù)已經(jīng)傳到了第五代朱軍岷手中,朱家百年的歷史仍在延續(xù)。我相信,熔銅藝術(shù)也會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輝煌!”
朱軍岷大師作品《盆中的果樹》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