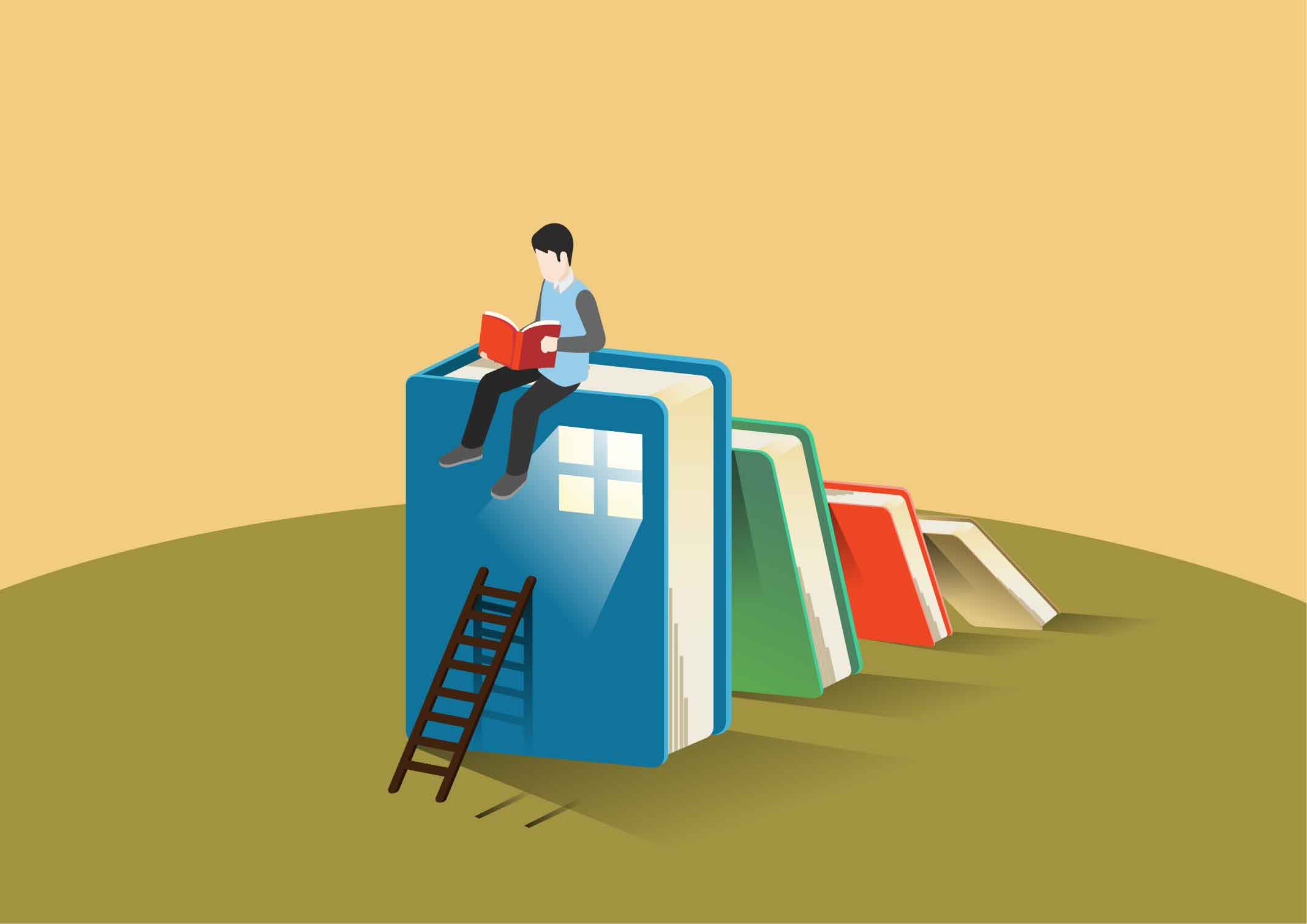縱觀全球種子安全局勢,阿根廷、墨西哥和印度的大豆、玉米和棉花等種源長期受制于人的教訓,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作為農業“芯片”,種質資源和種子安全對于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如果長期依賴進口,“洋種子”不僅價格高,更隱藏著真假難辨、質量難保以及“斷種”的風險。
既要藏糧于地,更要藏糧于技。我國高校尤其是涉農院校作為農業學科研究和育種人才培養重地,對于促進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提升種質研究實力應擔負起應有的責任。
“種業是一個產業鏈,是從基礎理論研究到育種、選種、種子加工再到銷售,其中強化前端非常重要,就是基礎性的育種理論、專業知識和研究。”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林萬龍表示,突破“卡脖子”技術,需要高校提供科研和人才力量來支持。

突破種質資源“卡脖子”——緊跟前沿科技突破基因育種關
據《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報告2021》分析,中國農作物種子具有“谷物強、經濟和園藝作物弱”的特征。牧草和蔬菜種子的年貿易逆差均已經超過1億美元。大豆進口量繼續保持高位,玉米進口增長迅速……
農作物種子依賴進口,可能隨時會面臨“卡脖子”風險。那么,種子的“卡脖子”究竟“卡”在了哪里?林萬龍告訴記者:“‘卡脖子’首先是卡住了種子的源頭,種子安全的核心是將‘原原種’掌握在自己手里。”
對于小麥、水稻等中國傳統作物來說,我國高校的研究團隊已經在進行種質資源的收集工作。早在上世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就在各地進行種質資源的調查和收集工作,目前已從國內外收集了3萬多份小麥種質資源,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來對基因進行挖掘,創制新種質。2018年,世界上首個完整版六倍體小麥“中國春”基因組圖譜完成。這項轟動世界的科研成果由來自20多個國家70多家機構的200多位科學家共同參與,歷時13年。作為唯一的中國團隊,西北農林大學的科研人員完成了其中7DL染色體物理圖譜構建及序列破譯工作。
但是,對于一部分作物來說,種源呈現“先天不足”。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賴錦盛長期從事玉米種子研究,他強調,玉米起源不在中國,大部分野生種質資源只能從美國、墨西哥等國家進口。
除了種源問題,種子的研發和生產以及種質資源發掘、保護與創新技術、新品種培育技術、種子生產和加工技術等,都是種業發展的“卡脖子”技術難題。
從2018年開始研究基因編輯技術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吉萬全表示:“我們的目標從過去的高產走向了高品質,所以生物育種、基因編輯、技術研發更重要。研發出的種子既要產量高、抗病,又要節肥節藥,還要吃飽、吃好、吃健康。”
“然而,種子基因編輯技術領域的專利大多掌握在外國企業手里。”山東省種子有限公司董事長邵長勇告訴記者,中國育種專家如果想使用某項技術,需要給相關外國企業交專利使用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種業被“卡脖子”的關鍵。
當前,育種核心技術攻關,是我國農業科技自立自強、保障糧食安全、確保不被“卡脖子”的關鍵。因此,對于高校特別是涉農高校來說,需要緊跟世界前沿技術,在基因編輯、生物育種等基礎研究層面來破解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
“在事關種業長遠發展的重大基礎科學問題闡析、基因資源深度挖掘與創新、前沿關鍵技術研發等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應作為主體。”賴錦盛建議,“我們要優化種業科技創新體系,不斷激發創新活力,做好種業高新技術和高端人才的儲備。特別是要鼓勵青年科學家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提升我國種業原始創新能力。”
今年1月,海南省三亞市人民政府與海南大學共建海南大學三亞南繁研究院(以下簡稱“南繁研究院”)。作為國家重點實驗室,南繁研究院將為國際國內農業領域的頂尖專家提供世界一流的基礎研究平臺、科研服務系統、交流平臺。海南大學熱帶作物學院院長羅杰分析,研究院還將為國家種業安全、糧食安全提供自力更生的科學保障,突破相關領域的技術封鎖,解決農業領域方面“卡脖子”的技術問題。
瞄準現代種業發展趨勢——夯實復合型高端種業人才基礎
人才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最寶貴的資源,是我國種業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保障。
然而,現階段我國種業人才仍存在很多問題。邵長勇介紹,我國種業人才隊伍中具備高素質的企業管理人才不足,復合型、創新型人才不足,掌握核心技術的人才較少,國際戰略型種業人才匱乏,無法為我國種業發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撐。
新形勢下,精準化、高效化、智能化,種業技術革命正在驅動現代育種技術迭代發展。種業研究人才儲備是否充足,直接決定著我國農業“芯片”技術發展勢頭如何。
“突破基因編輯、全基因組選擇、干細胞育種、智能設計等現代種業的關鍵核心技術,種業研究需要高精尖復合型人才支持。”林萬龍告訴記者,現代種業的人才培養從知識結構上來講,需要深入到分子生物學、合成生物學等方面的知識。合成生物學中不僅包含了生物學的知識,還有信息學、化學、工程學等方面的知識。
可見,現代種業人才既需要有扎實的基礎理論、生物學和生命科學的基礎,還需要廣博的知識體系。“農業其實也是一個高科技的行業,要把所有現代的科學技術集成應用于農業,才能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賴錦盛也表示,“信息技術、數據技術,也包括農業本身的生命科學和生物工程技術,都在新型農業科研和生產里得到體現。”
高校作為人才培養重地,在種業研究等基礎人才培養中肩負著重大使命。當前,高校需要打破學科壁壘,探索創新融合,積極探索種業基礎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和新形勢。
為此,中國農業大學開設了全國唯一的生物育種科學強基班。學生在大一到大三不分方向,強化數理化、工程學、生物學和信息學方面的知識;大四可以選擇研究生課程,與研究生階段打通培養,以此來實現農業人才尤其是種業人才的交叉融合培養。
今年,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也獲批強基計劃招生改革試點,實施生物育種強基計劃,探索建立多維度考核評價模式,選拔培養未來致力于國家種業科技發展和種源安全的拔尖創新人才。
在具體課程設置和教師配置上,高校同樣需要大膽的改革和突破,促進院校和學科融合發展。林萬龍建議,不應局限于現有的師資和課程,而要從需求出發,要從課程模式入手,打通傳統農學專業課程與信息工程、生命科學課程的融合。
針對育繁推“脫節”關鍵點——主動構建校企校地融合新模式
“同樣的種子,到了美洲以后推廣就比較快。原因是他們的種業研究、企業協作、科學推廣發展比較快。他們的科研能夠直接與‘下游’聯通。”被稱為“大豆院士”的南京農業大學教授蓋鈞鎰發現,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種業研究的發展。
從“卡脖子”技術突破到新品種的實地種植,中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邵長勇介紹,種子產業化需要把種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推廣與農業生產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將種子科技成果及時地應用于農業生產,它不僅能夠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速度,而且可以大大提高成果轉化的效益,從而有力地推動種子科技繁榮和種子產業、農業生產發展。
然而,與一些國家已建成全球布局的一體化現代育種體系相比,我國種業發展基礎研究、技術創新、品種培育的創新鏈與產業鏈有機銜接不暢。其中,種子的育、繁、推之間“脫節”的問題,也是制約種業技術研發的主要因素之一。
“面對‘卡脖子’難題,種業公司研發起步遲,能力和水平跟不上。”就大豆種業來說,蓋鈞鎰表示,企業起步遲,現有成果很少,談不上挖掘更先進的技術與研究。邵長勇也表示,我國種子企業缺乏自主研發的積極性,加之品種選育時間長、投資多、風險大,企業承受能力有限,進而導致了我國種子企業的科技水平普遍不高。
技術力量不足、創新積極性不高,導致我國主要作物的品種選育工作大多集中于高校和科研單位。對此,蓋鈞鎰建議,國家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培育大型種業企業來實現育繁推一體化;二是結合高校、農科院等上游研究單位來選育優質品種。
當前,我國種業發展急需由技術研發專家和產業應用人才組成的育種人才隊伍,需要將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推廣與農業生產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將種子科技成果及時地應用于農業生產。賴錦盛建議:“連接企業與科研院校兩個主體。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引導種業科技資源、科研院校成果和人才向種業企業有序雙向流動,實現科研院所、高校與種業企業資源共享、共用,促進創新要素的有效整合。”
有效的育繁推一體化育種機制,需要企業與科研院校共同發力。能夠掌握先進育種技術的農業研究型高校,也應該主動對接種業企業,做好科研對接與應用服務。
如今,一些高校也正在與地方共同探索種子的育繁推一體化模式。例如,南京農業大學利用在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產業引領等方面優勢,在海南培養高層次種業人才,組織引導學校科研團隊到海南開展一系列育種創新工作,逐漸探索出了一套校地合作的“南農模式”。
“企業與院校應形成融合機制,將力用在一個方向。”林萬龍認為,理想的校企合作就應該是雙向的,在高校師生到企業實踐的同時,企業也可以到高校里來,使大學的研究更有方向性和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