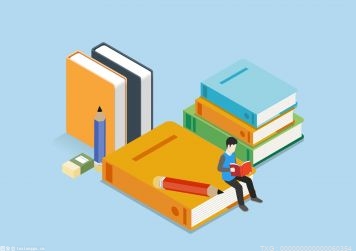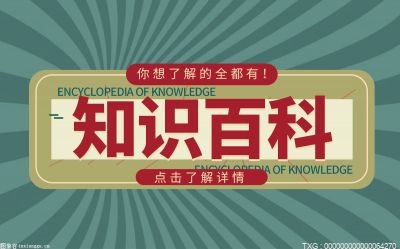8月31日,在沿著高低不平的山路行駛1個多小時后,記者終于從盱眙縣城到達了天泉湖鎮中心小學的龍山教學點,見到了3名正在報到的一年級新生——他們也是該教學點今年的全部新生。新學年,這里的67名學生,將在16名教師的帶領下,揚帆前行。
張克軍,是這艘“小船”的“船長”,自1982年從淮安師范學校(現淮陰師范學院)畢業,他已在龍山教學點工作了40年。因為他的堅守,當地的孩子們就無需前往40公里外的中心校上學,這為孩子們以及他們背后的家庭,減輕了不少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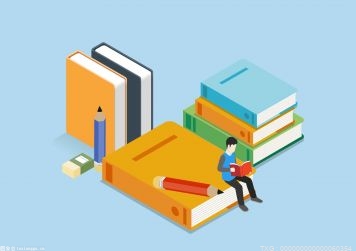
“只要有一個孩子,我都會堅持”
初到龍山任教,張克軍和父母的意見產生了分歧。父母認為科班出身的他,回到山村是“大材小用”,以后晉升困難,對象也不好找。但在張克軍的反復勸說下,父母妥協了。從那時起,張克軍就下定決心用自己的“留守”換更多山里娃的“高飛”。
雙胞胎仲維龍、仲維虎是龍山教學點六年級學生,自兩人入學以來,張克軍就變成了他們家的常客。5年來,在他的努力下,兄弟倆從考試不及格到門門過90分。兄弟倆告訴記者,在他們班的12個同學中,有9人先后得到過張校長的幫助,如買書包、贈書、課后輔導等。為了讓當地老百姓放心,張克軍把家安在了龍山,自己的孩子也在龍山上學。
在張克軍的教研筆記中,記者看到了這樣一句話:“生活皆教育,龍山的學生們如同色彩斑斕的花朵,每個孩子都具有獨一無二的閃光點。”小覃是名留守兒童,性格內向,在班里沒有存在感,張克軍就推薦他做班里的“鑰匙保管員”。此后,他每天為大家開門關門,第一個到教室,最后一個離開。他的一絲不茍贏得了大家的認可,人也慢慢變得自信起來。
劉生是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員,龍山是他求學生涯的第一站。從山村到北京,龍山給了他堅實的基礎,而這個奠基人正是張克軍。“在山村,有這樣一個有學識、執著治學的啟蒙教師,讓我受益至今。”電話中,劉生難掩激動。正是張克軍和同事們的默默努力,改變了像劉生這樣的許許多多山里娃的命運。
40年里,龍山從中心校變為村小再到如今的教學點,不斷“降格”;與此同時,張克軍的角色也不斷“豐富”:教師、勤雜工、司機……他曾有多次機會調離龍山,但依然選擇留了下來。“這么多年的堅守值得嗎?”面對記者的提問,張克軍說:“只要有一個孩子,我都會堅持下去。留下來,托住底,山村就有希望。”
培養標準不打折扣
只要時間允許,張克軍就不放棄任何業務培訓、進修的機會。控制授課時間、把握語氣語速、進行啟發式提問……堅持不懈的學習和實踐,讓他的教學水平不斷提高,在優質優課評選、教學論文比賽等活動中頻頻獲獎。2018年,他取得了小學高級教師職稱。在他的影響下,學校其他教師參加培訓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
為了讓孩子們獲得更好的教育,張克軍動了不少腦筋。20世紀90年代初,張克軍牽頭開設了書法、繪畫等社團(校本課程),并親自教授學生書法。他還因地制宜,變多年級“復式教學”為分年級教學,延長放學時間,提供課后服務,帶領孩子們從校園走進大自然,以美育心。生源剛開始減少時,他便敏銳意識到要“精耕細作”,鼓勵教師實施“精細化教學”,保證每名學生每節課有多次答題、發言的機會。由于部分學科缺少任課教師,張克軍除上語文課外,還先后擔任多門其他學科的教學工作,學生們都稱他是“全科老師”。
教學點雖然只有67名學生,但每年的“六一”兒童節他們都有節目參加全鎮的文藝演出,還有學生參加盱眙縣藝術節并獲獎。為了讓孩子們能夠更好地在舞臺上展示自我,張克軍和教師們每年都會早早開始籌備。沒有音響,就從附近的村民家借;沒有專業師資,就用電腦播放視頻,讓孩子們跟著一步步學;沒有足夠人手,就請求附近村干部來幫忙。
《少年中國說》是張克軍喜歡帶孩子們齊誦的一篇文章。吟誦時,張克軍常常紅了眼眶,“孩子們選擇不了出身,但可以樹立遠大志向,通過努力來改變命運”。現在67名學生中,有40多人的父母長期在外地打工,家訪、談心之余,張克軍堅持定期讓孩子們和父母視頻連線。“張校長的‘傻’是山娃的福。他的愿望其實很樸素,讓能飛的飛遠些,讓暫時飛不走的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培養好一個孩子相當于幫助了一個家庭。”天泉湖鎮中心校校長倪仕生說。
在張克軍的影響下,天泉湖鎮中心小學教師翟延欽和他帶領的英語送教小分隊,讓家長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翟延欽在中心校課務不減的情況下,義務前往教學點幫帶英語,每周兩天,駕車在近80公里的山路上來回奔波,今年已是第3個年頭。
“老伙計們”最牽掛的事兒
在教學點和張克軍共事的是一群年均58歲的老教師。如何帶好這群“資深”教師,張克軍有自己的辦法。在他看來,要想管理好隊伍,就必須以身示范。于是,張克軍見廁所臟便主動打掃,見有垃圾便拿來掃把,長此以往,大家心服口服。
在學校,張克軍像個“救火隊員”,哪里需要哪里跑。由于教師們年紀普遍較大,常有人因病請假。這時,張克軍總是二話不說,主動代課。每次前往中心校辦事,他也總不忘詢問,有無要捎帶的文件,有無要進城辦事的教師,他的私家車成了學校的“公車”。
同事姜文進說:“20年來,張校長堅持帶班、上課,但每年都主動要求將自己的績效工資降到一線教師以下,讓人十分欽佩。”這樣的做法,也讓龍山教學點的教師多了幾分責任感,少了幾分職業倦怠。“張校長‘吃的虧’反倒成了大家的‘動力’和情感上的約束力。”
已滿60歲的教師潘茂龍去年曾做過兩次腦部手術。第一次術后回家休養不到兩周,便返回教學點。然而,兩個多月后,他舊病復發,不得不做第二次手術。術后潘茂龍再也無法站上講臺,他便主動要求做教學點的門衛,“只要不離開這個教學點,天天看著這些孩子就行。”
如今,龍山教學點也配備了多媒體教室、錄播室等。教學條件變好了,然而教學點的未來依舊“命運未卜”。隨著越來越多的山民搬遷入城,教學點的生源還將不斷萎縮,老教師們也將在3年內陸續退休。教學點還能留存多久,還能守著這些孩子幾年,成為張克軍和他的“老伙計們”最牽掛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