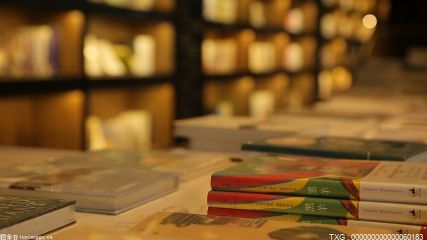英國哲學家波普爾說過一句話:歷史并無意義,是我們賦予它意義。毋庸置疑,教育也是如此。教育的意義來自每一個學生的成長,來自每一個教師對教育的認同,當然也來自那份師生共育的獨特情感。某種意義上教育的意義是師生情感結(jié)構(gòu)的顯示,是師生情感聯(lián)結(jié)的表征,是師生記憶的合體,經(jīng)由這些,教育的意義方能得到填充和生長。
一
作為一個極富理想主義氣息的教師,樊陽對教育的認識和他所進行的“人文行讀”總是能讓我想到很多經(jīng)典電影作品中的教師形象。比如《死亡詩社》中的基汀老師,他是永遠鼓勵學生發(fā)現(xiàn)自我的“船長”;比如《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馬修老師,他是用音樂啟發(fā)孩子性靈、重塑孩子靈魂的老師;比如《心靈捕手》中的藍勃教授和桑恩醫(yī)生,因為對威爾的始終不棄和積極治療才使一個數(shù)學天才得以成為自己;比如《魯冰花》中的郭云天老師,始終善于發(fā)現(xiàn)孩子獨有的天分。他們身上既有一些鮮明的自我個性,但同時更多地擁有師者的愛心和關(guān)懷。他們那善于發(fā)現(xiàn)孩子、幫助孩子、成就孩子的眼睛里總是噙滿了熱切的期盼,而樊陽也與之相似。
樊陽堅持人文公益講壇三十載,這套《行讀中西的人文課》(百花文藝出版社)便是他基于三十年人文行讀課程開發(fā)的經(jīng)驗和日積月累的思考總結(jié)而成,包括《先秦與軸心時代》《漢魏晉與古典時代》《唐宋與西方中世紀》《元明清與西方文明興起》四冊。
“人文”是一個略微帶有浪漫化想象的語詞,在現(xiàn)實中與技術(shù)、理性、分析等詞語擁有某種天然的“抵牾”,而這種“抵牾”情緒似乎也將其納入到了學科界限的考量之中。“人文”作為學科邊界的模糊地帶始終有一種自洽于各學科之間,但又矛盾于各學科之間的爭議性氣質(zhì)。而以筆者觀之,掩藏在這種“爭議”與“抵牾”之下的,更多恐怕是人們對評價標準的莫衷一是及其背后焦慮心態(tài)的反映。正如樊陽在2017年《語文學習》上發(fā)表的《刻在心靈的兩個詞:自由與慈悲》一文中所述:“……2005年后,我感到越來越多的壓力和束縛讓名著進課堂的語文教改無法推行,各種質(zhì)疑、反對遍布周圍,學生在學校沒有了讀書時間,很多老師、家長甚至認為讓學生看閑書怎么能出成績?沒有成績其他一切免談!”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在現(xiàn)實一線教學中進行“素質(zhì)教育式”的語文課改有多難,更奢談今日之“核心素養(yǎng)”教育,其中始終伴隨著這種“抵牾”與“爭議”的不正是評價標準問題嗎?因此,“雙減”政策的實施正是對這種長期以來“盤踞”在一線教學中的痼疾所進行的“正本清源式”的治理與整頓。
是的,仔細看上述這段文字,有一個詞——“成績”——始終如利劍一般刺穿著現(xiàn)實的教育,它與“人文”形成鮮明而熾烈的對比,似乎樊陽所進行的這場積三十年之功的“人文試煉”也難以抵擋它作為一種標準性判斷和價值性尺度的權(quán)威性。所以,我們需要反觀自問的是,難道“人文”天然是不具備某種標準性,或者說作為“標準性的人文”難以自恰于考試評價體系當中?我想如果真正要推進課程改革,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即推進考試評價體系的多元化策略與“人文”標準相結(jié)合。
二
從“語文小組”到“文學與文化講座”再到“人文講壇”,三個不同時期的名稱串起了樊陽職業(yè)生涯的三十年之變;從西安到上海,講述的是一個心懷人文教育理念的教師其職業(yè)地理的變遷;從上海行走到全國行走,將“體驗大地”的文明之旅化成了“還原現(xiàn)場的情景式學習”;從戶外到家中,對樊陽和學生而言,“師生在,處處皆杏壇”。這就是樊陽對教育的認知,他不斷地在教育教學上求新求變,終在探索的路上走出了屬于自己的“人文行讀”之風。然而,在這諸般變化之中,樊陽始終不變的是對理想教育之路的追尋。詩人泰戈爾說:“我們的教育宗旨必須是人的最高的目的,即靈魂最全面的發(fā)展和自由。”這不僅因應(yīng)了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人的全面發(fā)展觀,同時也契合了人的發(fā)展的自由理念。人的心靈何以發(fā)展,何以獲得“自由”,途徑只有“自由”本身,即“自由的行走才能鍛造自由的靈魂和發(fā)展的心靈”。
因此,我們必須打破單一、刻板、無生命的課堂教學,提供多元共融的課程內(nèi)容,以適應(yīng)不同階段和不同智力發(fā)展的學生的心理需求和現(xiàn)實需求。樊陽認為,在行走中落實“五育”才能真正展現(xiàn)“五育”重在實踐、重在學科融合的根本要義。“人文行走”便提供了絕佳的方式。如樊陽所言:“行走研學是德育引領(lǐng),智育閱讀研討貫穿,體育實現(xiàn),勞育、美育輔助的‘五育’無痕融合。”古人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言下之意即將“實踐”作為一種求知的根本方式存在于人們的心理意識當中,而樊陽所倡導的“人文行讀”正是以人文理念為指導、以實踐作為認知世界的根本方式所展開的思想領(lǐng)讀。
三
文史互證和文史互通向來是“人文”的核心理念。而將這一核心理念踐行的方式便是“行”,在“行”中才能突破自身因地理空間的限制而產(chǎn)生的思維高墻,不至于因?qū)W科壁壘和地理視域限制自身對人類文明的深度探索。《行讀中西的人文課》這套書里有一個隱藏且至關(guān)重要的概念便是“比較”的視野。某種意義上,文字的課程總結(jié)已經(jīng)超越了經(jīng)驗地理意義上的“行讀范疇”。“人文行讀”作為一種思維操練的方式在實踐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展,它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東方式的思考對人類經(jīng)驗和知識類群的把握,更多的是在一種縱向的地理跨越和橫向的線性維度上打開了我們對文學與歷史在地理維度上的全球化視野。
樊陽的“人文課”不受限于“宅茲中國”的地理概念,更多是一種整體的人類思維和文化的比較視野,不存在價值判斷,也沒有高下之別,只是作為一種文化觀照的方式在文學、史學、哲學的游走中獲得一種人文的浸潤,一種思想的震撼,一場春風化雨的甘霖。在這種“文化人類共同體”的概念觀照中,他引領(lǐng)學生更好地讀懂自身的文化符碼,也在認知自身的前提下“編碼”出更多有意義的經(jīng)驗世界和思想觀念。
(作者單位系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chuàng)意與傳播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2年03月16日第9版
標簽: 人文行讀作為思想試煉 meta name=d